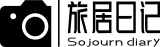叫扬叔,扬叔梗,苏超球迷,苏超梗图,足球整活,叫南哥,球迷热梗,叫扬叔官网,足球Meme,整活IP/叫扬叔(jiaoyangshu.com)是苏超梗圈爆火人物,整活足球圈、吐槽英超中超,靠一句“叫扬叔”火遍全网。这里是他唯一指定官网,集整活、热梗、名场面于一身,欢迎你也来叫一声叔!“苏超”的爆火与网络热梗“散装江苏”也有着种种联系,也因此引发球迷和网友的玩梗游戏。
所谓“散装”,当然只是一种网络戏称,指的是江苏各地级市间“谁也不服谁”的独特地域文化。这一文化在球场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宿迁对阵徐州被戏称为“楚汉之争”(暗合两地历史渊源),苏州与无锡的平局被总结为“苏州保住了太湖,无锡保住了机场”。另有意思的是,地级市下属县级区域的球迷有时还出现“反水”现象,在无锡对苏州的比赛中,隶属于无锡市的宜兴、江阴等地的球迷就公开为苏州呐喊,而隶属于苏州市的太仓等地球迷则为对手助威。那么,“散装”文化是如何形成的?除了戏称,如何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加以理解?一场接一场的“苏超”足球赛事也引出了诸多文化话题。
作为社会学家的陈映芳也在关注着“苏超”。在本期“聚落·场所·人”,她为我们讲述“苏超”之所以会产生种种网络热梗的历史与文化起源。
最近网络上广受关注的“苏超”,让江苏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了圈。而我在热热闹闹的话题中,不仅看到了上下各方自觉不自觉地致力于建构“江苏人”身份认同的意愿,还感受到了种种与“地方”相关的情绪。
“江苏”在中国,当然可以被视为一个地方,不过这儿说的“地方”,不只是作为政区(politicaldistrict)的江苏省,而是江苏内部的各个地方(place)。“政区”的划分及变化,通常是一种政治结果。它的规模、边界及行政级别等,历来主要由中央政府及地方上级政府来确定;而“地方”所涉及的,则是人与地域的关系,它包含的是与人及其社会/生活所关联的场所、区位和地方感等要素。尤其是人们的地方感,它需要由人的认同和情感等来确定。至于“地方情绪”,除了一般所理解的地方认同、地方情感外,我这里用以所指的,主要是围绕相关地方的历史地位、现实状况、地方利益和人们的地域身份等,人们所共享的某些集体情绪,特别是人们对本地方“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认知及不满。
不用说,政区与地方之间,不仅有融合,也会存在分异,后者是人类许多社会中的常态。在中国,如果说江苏省略有些例外的话,那就是它的政区与地方之间的分异,以及内部政区间、地方间的复杂关系更引人注目一些,或者说它们的典型性更为突出一些——在“苏超”之前,有关它内部的结构松散性,以及区域间的经济落差、文化差异,诸如“散装江苏”“十三太保”“苏南-苏北”(或“苏南-苏中-苏北”)等的地方现象,早已经广为人知。
地方情绪当然不只基层社会有,省会城市也不能例外。以这次“苏超”中的各种梗为例,南京与南通的比赛,曾经被称为“南哥之争”(到底谁是江苏的一号南哥),而南京与苏州的比赛,更被称为“宿命对决”(到底谁是江苏一哥)。南京虽然有一个与首都北京相对称的地名,历史上也有“六朝古都”的雅号,还曾是民国的首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央直辖市,但自1953年再度成为江苏省会以来,如今不仅其经济地位受到挑战——2024年苏、锡、常和南通四市位列全国GDP总量十强地级市;南京GDP总量居苏州之后,近年的增速且低于省内所有地级市。其作为省会城市的社会认同度还成了一个民间地域梗(由于地偏安徽以及对安徽省的经济社会辐射力,南京被不少江苏网民戏称为“徽京”)。
有一批尾大不掉、傲慢无礼的地级市的存在,这难免会成为南京人的一种地方情绪。但从其背景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明清以来政区影响力及地域社会的某些延续性(清代自康熙六年设江苏省,以江宁为省会,两江总督及江苏布政使驻江宁府,江宁布政使负责江宁府、扬州府、淮安府等苏北地区,直接受两江总督节制;而江苏巡抚驻于苏州,实际管辖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等苏南地区),更可以看到全球经济市场和现代型城市社会的兴起,对于人们重塑地方认同的强大影响力。
其实类似的地方现象、地方情绪不只江苏有,沿海各地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如福建省的厦门之于福州,广东省的深圳之于广州,山东省的青岛之于济南,辽宁省的大连之于沈阳……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分异,国家内部或地方政区内部的双城争霸现象,也是国际上常见的现象。
苏北地区的实力自证,可说是这次“苏超”的一个副主题。苏南与苏北的经济落差以及社会文化的各种区隔,曾是一个不无敏感的地域话题。在苏北地区,GDP总量排在最后一名(2024年)的地级市,则是连云港。
我最初知道连云港人对孙中山的特殊感情,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的。可能跟经济因素有关,在连云港我接触到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是本地人,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大多充满地方情感,且有着丰富的地方史知识。那天一位司机告诉我:“连云港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东方的港口大城市的,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有规划的。”
他非常肯定地回答:“那是由于江苏省政府不重视,因为连云港处在江苏省的边缘。”
后来我查阅各种资料,确实,孙中山早年曾考察过连云港(旧称海州)。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笔谈中他提到,“曾到彼地,盘桓七八天”。后来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中,他专门阐述了连云港地位的重要:“海州以为海港,则在北方大港与东方大港二大世界港之间,今已定为东西横贯中国中部大干线海兰铁路之终点。海州又有内地水运交通之利便,如使改良大运河其他水路系统已毕,则将北通黄河流域,南通西江流域,中通扬子江流城。海州之通海深水路,可称较善。在沿江北境二百五十英里海岸之中,只此一点,可以容航洋巨舶逼近海岸数英里内而已。欲使海州成为吃水二十英尺之船之海港,须先竣深其通路至离河口数英里外,然后可得四寻深之水。海州之比营口,少去结冰,大为优越。”按孙中山的设想,中国应在海岸建设三个头等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四个二等海港(营口、海州、福州、钦州),另外还有九个三等海港和十五个渔业港。此外,在中央铁路系统计划(二十四条铁路)中,以连云港为起点的就有三条路线——海州济南线、海州汉口线、海州南京线。(《孙中山选集·建国方略》)
连云港港口于1933年开港,如今是一个国际枢纽海港。但近代以来,作为一个曾有陇海铁路连接中国东西部地区的沿海港口城市,其港口的地位(无论是与早期的上海港、青岛港等比,还是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山东日照港比),以及城市的发展状况,都与人们的期望有明显的差距。对此,不仅连云港的市民感到难以接受——就像那位司机所说的,他们认为连云港受到了上级政府的不公平对待。在学术界,也形成一个独特的议题:连云港为何陷入“资源优而发展缓”的困境?这个问题甚至被称为一个“百年谜团”。
围绕这个议题,学者们的讨论涉及连云港历史上一次次的错失机遇(如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清末以来地方间的发展竞争、港口腹地的局限(连云港腹地多经济和资源相对贫困的地区),还涉及中央政府及省政府的各种决策对连云港经济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包括国家港口建设规划的变化,以及行政区划的一再变更(除政区划分变化及地位升降,连云港还曾于1948年被划归山东省,1953年重新划入江苏省后曾隶属于徐州专区)等。相关的研究中,历史学者的《不充分发展:1930年代以来的连云港港口、城市与腹地》一书,详细地梳理了近代以来连云港的行政区划演变和经济发展历史,其中特别分析了连云港百年来城市与港口之间的空间分离,还有港城各自的权属关系、管理体制等的变化。此外,对于行政区划、铁道线路等的变化如何导致连云港港口腹地受限,还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徐淮地区的经济功能的规定,以及江苏省经济发展史上政府对苏南苏北的区别性对待等,相关的解释不乏说服力。是江苏邳州人,从这项研究中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地方情感对其研究视角和剖析深度的影响,这也正是这项研究重要的学术价值所在。
一座城市、一个地方因为其历史上的发展机遇而怀念历史人物,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典型的就像南通市民对张謇的纪念那样。然而连云港人对孙中山的情感,却源于某种遗憾,是对一个历史梦想的追忆。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在连云港市政协的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议要为孙中山在连云港立一个铜像,并附一个纪念馆,以作为连云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那以后,连云港的民间一直就有呼声,希望能在连云港的海上云台山的山顶上建一个孙中山雕像。202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因为感念他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连云港建港计划,民革连云港市委会还特意组织拍摄了《百年回眸,先生所见即山海——民革连云港市委会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专题片》。(见微信公号《连云港民革》2025年3月12日推送文章,《连云港民革党员说“东方大港”——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
一个地方的历史情结中,往往沉淀有当地民众对自身状况的集体认知。如果对连云港的历史有所了解,我们当能理解,那是一种地方情绪的投射。
“苏超”比赛中另一个颇有意思的地方现象,是县级市/区的球迷对所属地级市的另类“反水”。例如无锡市对苏州市的比赛中,行政上隶属于无锡市的宜兴、江阴等地的球迷公开为苏州呐喊,而隶属于苏州市的太仓、常熟、昆山、张家港的球迷也纷纷为对手助威……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些理解为球迷间展示团结友爱情感的幽默方式。不过我也愿意相信,在今天的江苏省,人们对地级市行政管辖权的认可、对政区身份的认同,存在一些问题。事实上在视频中我还看到在一些比赛现场,不少苏南地区的球迷是特意身穿只标明县级市/区(甚至镇)身份的统一服装集体登场的。
“苏超”的确切定义,其实应该是作为政区的地级市联赛。众所周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江苏省在全国是最早试行“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一个省,后经过省内一系列的行政区划调整(包括将一些原省辖市或县城提升为地级市中心城、再将周边若干县划归其所属等方式),遂形成了如今稳固的“十三太保”格局。目前,地级市管辖的县级行政区还包括了一些被划入中心城区的“区”(原周边县/市),以及已经撤县设市的县级市。
而在现实中,自上世纪末开始,全国各地已经有一些省/直辖市开始了对市管县体制的改革。例如同样以经济发达而引人注目的浙江省——1992—2008年,浙江省选取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实施了“强县扩权”。2008—2011年,浙江省又进一步推进“扩权强县”,把下放权限惠及所有县市。
关于“市管县”行政管理体制在我国的演变历史,以及这一体制在不同阶段对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利弊得失,学术界曾有不少讨论和分歧。但自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国家逐步改革既有的市管县体制,重新确立省管县制度。其观点的依据,有的是基于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的根本制度;有的是基于地级市的行政成本以及这一纵向管理体制内含的计划经济属性(即基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有的是根据新世纪以来对一些分别实行“省管县”与“市管县”的不同地区的实证调研结果(省管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还有的则是基于县域社会对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性……笔者注意到,关于江苏省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少学者从纵向等级的政府间发展竞争、权责分配、财税关系、城乡统筹等方面,论证了在当下江苏,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市管县体制已经给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种种困境。事实上,民间早有“市压县”“地刮县”等的说法,连这次“苏超”比赛中的南京球迷也在镜头前不服气地说:“我们南京GDP不如苏州,是因为苏州靠了下面的县级市,而我们南京没有县级市。”
任何制度一旦确立,都可能形成其结构性延续的自身动力,以及相关利益方对制度的路径依赖。江苏有江苏的逻辑,而且江苏的行政体制、财税体制的改革也不只是江苏的事。
尽管如此,有一些现象仍然值得我们关注。以江苏、浙江的差异为例,2024年,江苏的GDP总量(13.7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二,而浙江屈居山东之后排在了第四(9.01万亿元)。可是,浙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7013元,而江苏是55415元。其中,浙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8251元,江苏是66173元;浙江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42786元,江苏是32414元。另外,浙江的人均财政支出是1.76万元,江苏是1.49万元,这说明浙江在民生领域的投入占比比江苏高出5个百分点。同样不应该忽略的,还有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地方自治,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城市间的关系平等,也是现代国家普遍的制度设置。
江苏各地的市民、县民(县级行政区内居民的泛称)对其政区身份的认同度到底是怎样的?这需要相关的意识调查才能真正了解。而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分化,地方认同、地方利益背景下的地方情感/地方情绪的存在及表达,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或许正是今天苏超现象的现实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