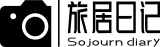叫扬叔,扬叔梗,苏超球迷,苏超梗图,足球整活,叫南哥,球迷热梗,叫扬叔官网,足球Meme,整活IP/叫扬叔(jiaoyangshu.com)是苏超梗圈爆火人物,整活足球圈、吐槽英超中超,靠一句“叫扬叔”火遍全网。这里是他唯一指定官网,集整活、热梗、名场面于一身,欢迎你也来叫一声叔!杨婶走了,她活了九十多岁,在我们这半道街也算是高寿了。她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坎坷。
杨婶本名王桂英,1930年生于太行山脚下的柿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是个老石匠。民国三十二年闹灾荒,杨婶的姐姐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后又被人拐骗到山西浮山,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男人。哥哥也饿死了,她和弟弟跟着父母奶奶去逃荒。她和奶奶一起走,走着走着,眼看着奶奶饿得走不动了,倒在路边,赶紧喊父亲过来,奶奶已经断气。父亲把奶奶背到一个废弃的窑洞里,草草掩埋。灾荒过后,一家人才又返回故乡。1949年杨婶嫁给了我的邻居杨叔。
杨叔是杨春广老人的小儿子,排行老四,小名四法。他的三个哥哥都已去世。大哥婚后留下二女一子,大嫂带着儿女远走山西。二哥三哥没有婚娶就去世了,据说他们是死于肺痨。杨叔结婚成家,了却了二老一桩心事。
1950年,杨婶生了个女儿,取名小翠。一家五口,虽不富裕,也其乐融融。为了生计,杨叔又跟着岳父学会了石匠手艺,农闲时出去给人锻磨,挣个零花钱。杨婶为人厚道,又勤劳能干,和我母亲交好,我们两家住得又近,就把女儿小翠寄给了母亲。小翠比我大几个月,小时候我俩常常一起玩儿。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杨叔的母亲有病去世,杨婶一人挑起了家务重担。杨婶的娘家有个弟弟叫来闯,结婚成家后,生了个女儿。由于照顾不周,晚上女儿被捂死了。门口的人奚落、自己的懊恼,来闯精神受到刺激,得了个精神分裂症。杨婶又多了一份牵挂,时常往娘家跑,帮助父母。
杨叔的大嫂年轻时候,颇有几分姿色,缠着小脚,做得一手好针线活,老公公还对人炫耀这个儿媳。可是后来的一件事,彻底颠覆了老人对大儿媳的看法。那是他们刚结婚时,和公婆三间屋两头住。公婆原来住的那一间北屋,稍好一点,让给儿子作了婚房,自己挪到了南间。有一天晚饭后,老公公端个煤油灯,下意识地走进了儿媳的房间。刚进门,大嫂马上厉声质问:“你来干啥?”公爹一惊,立即不好意思地退了出去。可是大嫂却不依不饶,拿个脸盆到街上敲着吆喝:“东邻西舍都听哩,我公公掏锅底灰......”弄得杨春广老人又气又恼,立即和大儿分开另过,并从此不待见这个大儿媳妇。
虽然不待见大儿媳妇,可是孙子孙女还是自己的。老伴去世后,杨家爷爷吩咐杨叔去山西把大儿媳妇和孙子孙女叫了回来。回来时还又多带回了个小女儿,小名伏英,和小翠同岁。刚回来时,他们住在别人家,后来搬回家住。杨爷爷不准大儿媳住里院,只让她住在二门外的一间小屋里。
杨叔虽然和嫂子有过矛盾,可是对待侄子小奎还是挺上心。小奎在农机厂上班,因为家穷快三十岁了还没讨到媳妇。杨叔到处托人,张罗给侄子找对象。后来终于给找了个离婚对象,并很快结婚生子。大嫂去世后,杨叔的侄子侄女、侄孙、侄孙女都和叔婶亲近来往。
转眼到了大办钢铁年代,杨叔的老父亲也病倒了,当时的条件普遍不好,也没去医院诊治,没几天就去世了。埋葬了父亲,杨叔家里只剩三口人了,空落落的。别人家的孩子都三五成群了,自己家还是一个女儿。三年自然灾害过后,杨婶就和杨叔商量准备抱养一个儿子。杨婶有一个亲戚叫靳德贵,在县医院当医生,杨婶就托他留心帮忙。
1963年秋后,杨婶的亲戚捎信来说有一个临盆的产妇生病住院,欲将自己所生孩子送人。杨婶闻讯立即赶到医院,第二天就把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抱了回来。一般人家抱养孩子都是等小孩半岁或一岁以后,能吃米面才抱回来的。杨婶为了养活这个孩子,真是费了老鼻子劲儿。新生儿需要母乳喂养,可是没有母乳,杨叔赶紧去城里买来炼乳。杨婶也服用了下奶的“妈妈多”等药,可是自己没生产,奶水不下来。杨婶一个月除了上厕所几乎没出过屋门,日夜精心照护这幼小的生命。邻里来看望的都说杨婶比自己生孩子还辛苦淘精神,人瘦了一圈。婴儿没有奶吃是个大问题,吃炼乳一般农村人家买不起。杨叔听说羊奶好,就去买了一只奶羊,可是奶羊没有生羊羔时也没有奶水。没有办法,杨叔杨婶只好下狠心出钱给孩子找个奶妈。刚好打听到城东街有个人家生了孩子没有成活,有奶水。杨叔两口就把孩子送到那一人家,每月给人25元。25元今天还不够一盘菜,可是当时却是一项大开支,两个人凭挣工分一月也难挣30元。那时能用起奶妈的都是高干。
杨叔杨婶省吃俭用,农闲时磨豆腐、卖豆腐,杨叔锻磨,想方设法挣钱。每个月去给奶妈送一次钱,把孩子接回来停上半天再送回去。孩子长得倒挺可爱,胖乎乎的很敦实,我曾和小翠一起去东街把孩子轮换着抱回来一次。孩子能吃面食后断了乳,被接回了家,奶妈自然成了孩子的干娘。
俗话说,三冬三夏,才成娃娃。杨婶含辛茹苦,把儿子养到两三岁,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谁想新的磨难接踵而至。那年夏天,杨叔老是咳嗽,去村医疗所拿了药,吃了也不见效,直到一天晚上咳得不能睡觉,还喀出了血,第二天去县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肺结核。肺结核被人们说成是富贵病,不能干活,还得花钱,除了打针吃药,还得吃好的营养。杨婶没有抱怨,农闲时加入了更加繁重的体力劳动队伍一一用平车去煤矿往电厂拉煤挣钱,供杨叔花销。煤矿到电厂来回三十多里,每天拉一趟煤,能挣一块多钱。那时拉煤的人群里,只有杨婶一个是女的。小翠也不上学了,回来挣工分。
杨叔看到自己的女人为了自个儿吃苦受累,心里不是滋味,就去求跟自己家关系好的放学早的学生去半道上帮杨婶搭把力。那时我上高中,有一次星期六下午放学回来早,还去接过杨婶。那天我一回到家,见杨叔站在院子里。妈妈对我说:“你去接接你婶吧,从老谭那儿(也就是柿槟村西)往下,路有点上坡,你婶太不容易了。”我顺着公路往上走,走到柿槟村西,就迎着了杨婶他们几个拉煤的人。只见杨婶汗流浃背,吃力地拉着满满的一平车煤,有一千斤上下,不住地用毛巾擦汗。我赶紧拿出绳子拴在平车上,帮杨婶把煤拉到电厂。那时我觉得杨婶是我们村最能干的女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集体化时期,农民主要靠挣工分分粮、分红。虽然土地不少,可是土地贫瘠产量很低,而且大部分种了红薯,打下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卖余粮,生产队还要留些储备粮,所以毎人分得的细粮(小麦)很少,只有一百多斤,根本不够吃,连过年时蒸的馍也是掺了一半白玉米面,平时更是不敢多吃。剩下的多是红薯、玉米之类。杨叔不能干活,儿子还小,只有杨婶和女儿小翠两个女劳力,工分自然不多。我们东边的温县是小麦主产区,他们的麦子除了自已吃还有剩余,所以我们村的一些男劳力拉煤挣下点钱,就骑自行车去温县买小麦。杨婶也想买点补贴杨叔,可是自己不会骑车,她想到了自己的干儿子,也是本队的街坊,就央求干儿去替自己跑腿。
杨婶起早给干儿做好饭,又烙了饼当干粮,目送干儿等一杆人上路。天黑的时候,买粮的人才回来。杨婶万分感激,等干儿走后,她掂起那多半口袋麦子,总感觉有点少,仔细一看,原来口袋角有个小洞,是被自行车辐条磨破的。麦子少说要漏掉几斤。杨婶心疼得直掉泪,可还是忍住没有吭气。
杨叔有病后,每天需要打针,开始时候去村医疗所打,时间长了,也不想老麻烦人,杨婶就学着自己给杨叔打针。刚开始不是扎得深了就是浅了。有一次扎得浅了,药水顺着肉皮流了出来,赶紧又往里扎了扎。
杨叔有些小家子气,杨婶也是个有个性、要强的人,他们有时候也闹矛盾。还是杨叔生病前,有一次,杨叔出去玩牌,回来已是深夜,杨婶就把门上住不让进屋。杨叔在门外喊:“小翠,小翠,快把门开开......”而杨婶则在屋内厉声说:“谁也不能开门,敢开门试试......”弄得女儿左右为难。那时我晚上跟小翠姐睡,听到他们吵架也很害怕。
杨叔生病后有一天杨婶正在做饭,还是夏天火炉在院里房檐下,杨叔为了一点小事又和杨婶吵了起来。杨婶气不打一处来,手中正拿着一只碗,就朝杨叔头上砸去。俗话说:碗是一只虎,碰头血必流。碗烂了,杨叔的头也破了,鲜血立刻顺着脸颊往下流。杨婶见状慌了,连忙上前捂着伤口说:“去医疗点包包吧!杨叔赌气地说:“不去,哪怕死掉呢!”杨婶央求道:“老爷吔,快去包包吧,哪怕回来我去住教育所(即看守所)哩。”
杨叔他们家多年前应该是家境不错的,从他们家的高门楼、四合院以及门前的上马石可以看出。到民国时期,家道中落,上房和临街房先后倒塌,只留下东西厢房,还有那一级一级的条石台阶和青石门墩。这里农村有个说法,院子没有上房相当于没有主房,对家里的男主人不好。这也是杨叔的一块心病,多年来他一直想把上房盖起来,可是苦于没条件。焦枝铁路修通后,火车站就建在我们村西。国防三线和机场相继上马,火车站装卸的物资较多。李庄村的人有了一份装卸火车的活干,劳动工分值也高了一些。一些住房紧缺的人家、劳动力多的人家就开始盖房。那时盖的还是土墙的房子。盖房要自己备料,请人帮工。大工也就是木工要付工钱,小工光管吃饭不要工钱。
杨叔两口节衣缩食,几年下来,又有了一点积蓄,便着手盖上房屋。他们自已先把原房地基的石头挖出来,把地基清理干净,又请人打了夯,把房根基扎好。接着拉土,请外地的专业人员垛墙。垛墙分四次垛好,每垛好一节还要用麦草把墙遮盖起来防止雨淋,等一段时间,待墙干了,再垛上面一节。四节墙都干透了,才能盖上坡。差不多一个春天,才把房子盖起来。上面的瓦先干摆上,第二年才又瓦好。盖房子要管匠人吃饭,杨婶宁可自已家人伙食次一点,也要让匠人吃好、吃饱。给他们家帮工的人都说杨婶家的伙食比其他人家好一些。这期间,许多活都是杨婶亲力亲为。
房子盖好,已是七十年代中期,杨婶的女儿小翠也二十多岁了,该出阁了。经人介绍,小翠找了个婆家,是城南街的郝家,丈夫郝福东,在化肥厂上班。那时他们家的条件并不好一一没有公爹,婆婆瘫痪在床,还是哥哥嫂嫂帮忙张罗办的婚事。婚后没多久,婆婆就去世了,兄弟俩也分开另过。第二年小翠生了个儿子,因为没人帮助带孩子,经常住娘家。后来孩子稍大一些,小翠就在街上摆摊,卖鸡蛋、水果等。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南街许多人家开了商店,尤以批发部居多。小翠家的院子刚好临街,有一间房子可以做店面,他们家也顺应潮流,开了家批发部。
他们家的批发部商品齐全,价格合理,好多乡下的小卖部都来这儿进货。批发部的生意越来越好,小翠的爱人也辞职回家干起了个体。自己家的人忙不过来,就请亲戚来帮忙。杨婶的妹妹、侄女也来了。杨叔的儿子小海中学毕业后,也来店里帮忙。经济条件逐渐好转,小翠家把原来的旧房子拆了,盖了新的混砖楼房。1984年,杨叔杨婶也张罗给儿子小海娶了媳妇。媳妇李蕊娘家是轵城南岭背坡的。娘家老人的人品很好,李蕊人也贤惠。婚后几年先后生了一女一男。杨婶两口喜不自胜,虽然受点儿劳累,也心甘情愿。
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开始实行住房统一规划,原来的土房子逐渐拆除,盖成一家一院的混砖两层楼房。1987年,杨叔他们家也拆了原先盖的土房,盖了一处独立的小院,两层楼房。这次盖房自己家只管备料,由建筑队负责施工。他们家旧房子拆下来的木料、砖石都可以利用。况且儿子也大了,杨叔两口没费多大腰劲。新宅院盖好,刚好孙子降生,杨婶只是尽心照顾孙子孙女。
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家务都是杨婶承担,杨叔的手拿惯了锤子、凿子,干起家务活来笨手笨脚。杨婶一半抱怨地说:“我就是那一辈子的老炊,死灶火,埋锅底,没有人帮忙。”杨叔抱歉地说:“小翠妈,这些年真辛苦你了,以后我帮你做饭。”杨叔说得诚心诚意,杨婶听了感动得想流泪,把这些话对街坊邻居们说了一番。
其实,杨叔也没怎么帮助杨婶。新房子住进去不到一年,杨叔又有病了,这次杨叔患的是胃癌,并且是晚期,不好医治。杨婶精心照顾,端汤倒水,也没能挽救住杨叔的生命。1989年,杨叔走了。他只活了六十岁,比他的三个哥哥寿命都长,也见到了孙辈,该瞑目了。
等孙子断了奶,儿媳也去小翠的店里帮忙。杨婶除了照顾孙辈,还要耕种队里分包的责任田和几分菜地。那些担大粪、翻地的重活都是杨婶亲力亲为。有一年夏天杨婶去种菜,为了方便,把鞋子脱了。她赤着脚往后退,一下子踩在十指耙的尖上,把脚底扎了个窟窿,顿时鲜血直流。旁边种菜的邻居闻讯把她扶到三轮车上,拉去包扎后送回了家。菜地里的活没人干,还有秋庄稼要锄,杨婶只好请自己的妹妹来帮忙。
小海和媳妇李蕊在姐姐的批发部帮忙,每人每月薪酬五百多元,这在当时已经很不少了,可是他俩不甘寄人篱下,想自己单独干。杨婶不同意,娘俩还吵了一架。终于他俩还是自己租了个门面,从姐家的批发部搬货来卖,不用投资轻松赚钱。村里有人羡慕小海有个好姐姐,有人夸小海脑子灵光。
后来火车站、化肥厂扩建,把我村的地征用完了,也不用种地庄稼了。只留了一点菜地。儿女们不让杨婶再种菜,可是她干惯了活,闲不住还是坚持种。她已经六十多岁,担不动大粪了,就把粪桶绑在三轮车上,拉到菜地。除了种菜,还有大把的空余时间,杨婶就约几个人在家里打牌消耗时间。最初玩的是小骨牌,后来换成麻将。先是几角钱的输赢,后来到几元,十几元。她看到村里有人去北京旅游,也想去,女儿就专程陪她去了一趟。
时间如白驹过隙。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迅速发展,小海干了几年商品批发,积攒了一些钱,可仍不满足,又与人合伙在轵城承包了个榨油厂,生产大豆油、菜籽油、葵花籽油。有了钱就任性,小海又嫌自己住的房子太小——还是和以前的老房子格局一样,一明两暗,跨度也小。就把杨叔在世时盖的混砖房拆了,重新设计,盖成了三层框架结构的别墅型房子。新房子盖成后,小海让老妈住最好的向阳房间,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并且有室内卫生间。
小海发达了,也想在村里的政治舞台上露个脸。他参加了村里的干部竞选,当上了村委委员。
杨婶的孙女芳芳出落成了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大学毕业后,在妇幼保健院工作,结婚成了家。孙子杨建毕业后也干起了企业。杨建的舅妈是济源有名的化妆品大咖解小平,她家的生意做到了深圳。杨建先是制作洗衣液,利润颇丰,后来又开了几个店面。杨建结婚时,他的外公就添了十几万。家里的高档家具、轿车、电器一应俱全。再也不用为钱的事发愁了,杨婶感叹地说:“真想不到,这社会变化太大了,也太快了。不管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啥东西都用之不尽。”很快重孙子也诞生了,杨婶四世同堂,每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杨婶过上了幸福生活。可是她的腿脚却不灵便了。“年轻不惜力,老了没熬头”。也许是年轻时出力太大,或是老年人的通病,杨婶的腰腿疼痛逐渐加重,走路困难,虽多方求医,却见效甚微。儿子就给她买了一辆轮椅,外出的时候儿子媳妇一起推着她去。小海对老妈可谓孝顺,每天不管回来多晚,都要到母亲的房间看一眼,叫一声妈。杨婶的两个重孙子活泼可爱,和老奶特别亲近,每天一回家就老奶老奶地叫着,并为老奶表演节目,杨婶高兴得合不拢嘴。
杨叔有一个小叔叫杨春敏,年龄和杨叔相仿,解放初参的军,后来转业到天津工作。他们家的老院有一半属于这个小叔的祖业,包括杨叔当年盖的土屋。农村住房统一规划后,有些人在外地的也回来申请盖了新房。小海为此专门去了一趟天津,征得小爷同意,申请了一处宅基地。小海又花了两万元给小爷买墓地,后请人设计、施工,又盖成了一处宅院。
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杨婶的儿子小海被查出了胃癌。同时儿媳李蕊也被查出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他们双双去了郑州求医,先给李蕊作了微创手术,又给小海作了胃切除手术。手术后两人恢复得还不错,他们还一起外出旅游。小海是个比较随性的人,他不懂胃病是要养的,还是胡吃海喝,老娘劝说他也不听,结果旧病复发。虽然二次作了手术,可是已经晚了。2022年5月,小海走了,还不到六十岁。
白发人送黑发人,杨婶老年丧子,情绪低落,常常叹自己命运不好,疾病也随之找上门来。她常常感到肚子疼痛,去医院检查查出了胆囊炎。保守治疗了一段时间,有了好转,可是没有根除,不到一年,又复发了。这次医生给她作了一个搭桥手术。九十多岁的人了,经不起折腾,这次杨婶没能扛过去。2023年9月,杨婶走了,享年九十四岁。
杨婶,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一生没有干过什么大事,只是以自己的一己之力,维护着这个家庭的和谐、稳定,促使它兴旺、发展,诠驿了和、孝、善的真谛。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宗馥莉“首战”输了?并没有!十个关键问题读懂宗氏子女18亿美元“信托纠纷案”
已清空所有美股!传奇投资家Jim Rogers重磅发声,“下一次美国危机将是我有生以来最严重的”
武汉某大学优秀校友:方方、王懿、杨景媛、黄思晗、周玄毅、选调生顾某……
以色列公开独立,不足一天时间,中方反击随即而至
警方上门监控视频曝光,广西“亮证逼迫让路”事件“让路男”还原事件经过,再发声:希望纪委介入调查,女子公开道歉
《编码物候》展览开幕 北京时代美术馆以科学艺术解读数字与生物交织的宇宙节律
亚洲第1人!巅峰孙兴慜2020年身价9000万,28岁差一点成亿元先生
山东省教育厅2025年普通高考第三次新闻发布会,双录取考生按时进行录取确认,逾期不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2025年高考录取资格
山东省教育厅2025年普通高考第三次新闻发布会,加强宣传服务,高效回应考生关切